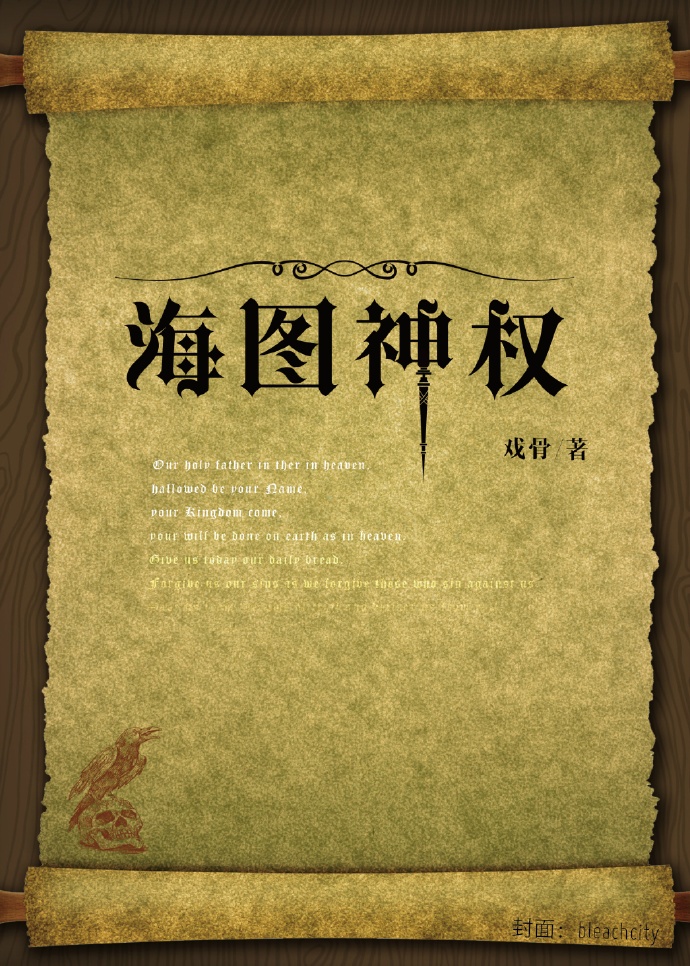“之前說到,夢魇号一直在外開辟新航線,竟然有人膽敢在黃金航線上冒充他們?”
“那些海盜船将夢魇号團團圍住,每一艘上面都有虎視眈眈的大炮!”
“隻見猩紅玫瑰從身後拔出一把匕首,揉身抓住了一根纜繩,就這麼單槍匹馬朝着對方的船上蕩了過去!”
“說時遲那時快!對方的船長舉起了一把強弩,瞄準了她的腦袋!”
……
門被突然用力推開,巨大的聲響分毫沒有影響正在興緻勃勃聽吟遊詩人傳唱猩紅玫瑰事迹的好事群衆。
畢竟這裡是朝着東方大陸前去的必經之路,操着各種各樣口音的人分毫不少,瞧瞧那邊,四桌說着五種方言,誰特麼知道隔壁桌在說什麼?
就連吟遊詩人都隻能撿着能聽懂人最多的列支敦語講故事,誰讓自從猩紅玫瑰将航道徹底打通之後,就屬列支敦國的商船來來往往最多,這女人可不得了,和納瓦拉的博杜安家主居伊共同把持了萊曼群島,和納瓦拉形成了一個商圈鍊,更要命的是,她還和列支敦國共同搞了一條所謂的黃金航線,把海盜們統統趕到了另一條線路上去。
誰要從東方大陸倒賣貨物過去,除非是冒着天大的風險從另外一條毫無保障的航線上,冒着被那群窮瘋了的海盜血洗的風險,否則根本沒辦法逃過她的手心,要說這裡頭沒有教廷的推手,誰信?
列支敦國可都從原來的毫無信仰轉變成教廷的狂信徒了!
猩紅玫瑰和黃金主教的绯聞,從來都是這群人最樂此不疲的話題。
進來的幾個人都是黃皮膚黑眼睛,個個都透着一股子的彪悍之氣,雖然身量不高,但是虬結的肌肉充分說明了有多麼的不好惹。
是在海上跑久了的老油子……随着東方航線的開通,也越來越多的東方面孔出現在了這裡,那可是流淌着黃金與香料的肥美之地,他們的出現,往往都代表着巨大的利潤。
不少人的眼睛登時亮了。
他們身後跟了個年輕的僧人,英俊的面容引來了不少注意,甚至有人投來了□□的視線,就像一條粘膩的舌頭一樣在人身上來來回回掃了好幾遍。
在海上待久了,又沒有女人,多的是人在漂亮的男人身上找樂子,就算平常喜好是女人的,憋久了也不介意拿男人開開葷。
何況這個細皮嫩肉的和尚?
人多的地方是非就多,更别提還是在這種魚龍混雜的地方,人壓抑久了,就總愛找點樂子,哪怕是作死也一樣。
“吹的吧,”一個彪形大漢嗤之以鼻,“猩紅玫瑰再怎麼也不過就是個女人,能抓着纜繩蕩那麼遠?”
“還說不定是不是陪人睡出來的呢!”
這幾句沒腦子的話登時引來了聽衆的不屑,“哪來的鄉下人?猩紅玫瑰都沒聽過?”
“别理這些沒見識的,繼續說繼續說,然後呢?”
“哎呀怎麼可以用□□呢?太沒有騎士精神了!”
“就是就是,一看就不是什麼正經海盜船!”
大漢:“……”
……是他腦子不對還是這群人腦子不對,都他媽是海盜船了,誰跟你談騎士精神,有病嗎?!
大漢悻悻地坐下,當做沒聽見那邊此起彼伏的詢問聲,難以置信地搖搖頭,跟同伴抱怨了一句。
“都他媽瘋了,把一個女人捧的那麼高。”
同伴嘲笑道,“有本事你也開辟一條新航線?那他們馬上就來追捧你了。”
大漢是第一次來這裡,雖然聽說過這條航線的來源,可還真不知道猩紅玫瑰竟然闖出了這麼大的名頭,在瞠目結舌之餘不免也有些生出了好奇心。
“那航線真是她開的?”
“你以為?”同伴一揚脖子把那滿滿一大紮啤酒灌下了肚子,然後才伸手擦了擦嘴角的泡沫感歎道,“猩紅玫瑰,那可不是個簡單的女人……這往歐拉大陸去的幾個重要中轉島嶼都和她有關系,不說别的,就說她弄來了那麼好的啤酒我都要愛死她了!”
大漢有些懵懂,幹脆轉而去聽吟遊詩人繼續講故事。
眼看湊過來的人越來越多,那吟遊詩人的轉了轉眼珠子,講到最□□的時候突然停了下來,朝着周圍的人連連做了好幾個揖。
“哎呀各位,看我也說的這麼口幹舌燥了,能不能請各位賞點酒錢?”
這是慣例了,有錢才繼續說下去,給的錢多了,還能直接點自己喜歡聽的故事。
很可惜,聽的人雖然多,但是舍得掏錢的人卻不多。
吟遊詩人連都快要笑僵硬了,這才有人稀稀拉拉給了幾個錢,這次的聽衆都不算太大方,湊過來白蹭聽的人可不少,尤其是之前那個還嗤之以鼻的大漢,他一個人就占了三個人的位置,偏偏還就不給錢。
吟遊詩人暗罵了一聲,草草地結束了故事,打算換一家酒館再試試。
他走出酒館,外面依然是酷熱的海風,烈日晃得人的影子在腳下隻有那麼小小的可憐的一小團,吟遊詩人伸手擦了擦額上的汗水,忽略掉嘴上因為幹燥而裂開的血腥氣,打算快步走向另一個酒館。
再怎麼,也先喝上一杯吧。
“請等等。”
可就在這個時候,一個人攔住了他的去路。
吟遊詩人有些詫異地擡起眼,面前年輕的僧人一身寬大的僧袍,這裡是終年酷暑的島國,幾乎所有的當地土著都是皮膚黝黑,隻在身上穿着最最短少的布料,無論男女。
也正是因為如此,僧人的裝扮顯得尤為的奇異,他的僧袍有些舊了,但卻依然很幹淨,或者說是整個人都透着一股幹淨的氣息。這和這裡的人身上常年彌漫着的汗臭完全不一樣,硬要描述的話……應該是帶着一股子與世無争的淡然。
可惜吟遊詩人對男人并沒有什麼特别的愛好,他隻是皺起眉,“你有什麼事情嗎?”
太陽太曬了,他還想找個地方好好的休息一下。
“是這樣的,”僧人微笑了一下,“我付你報酬,想請教您一些問題。”
吟遊詩人最近的收入都不太好,他狐疑地看着僧人,這些人一般身上可都沒什麼錢,他之前已經受夠了這群窮鬼,态度當然不算太好,反而透着股斤斤計較的意味。
“你出多少錢?”
“一個金币。”僧人意外的很大方,甚至垂下的眼簾都帶着一絲彬彬有禮,“您滿意嗎?”
“成交。”
事情還要追溯到一個月前。
僧人從悶熱地船艙裡出來,趁着夜晚到海面上透透氣……這裡和他待慣了的環境當然不能比,不過在那樣的環境下,能從天家的手中逃出生天已經是僥幸,能有這樣的一條船已經是走了大運,哪裡還能再挑剔别的?
現在流落到這個地位的自己,恐怕也比一條喪家之犬好不了多少。
僧人皎皎如月的清俊臉上也露出了輕微的愁容,想起那個人……他輕而又輕地歎了口氣。
如果有機會回去。
……他又如何有臉再回去?
煩悶的思緒當中,海面上忽然傳來一聲嘩啦的入水聲,有好生之德的僧人擔心有人不慎落水,急忙走到了船邊往下看去。
可這一看,登時被入眼的極緻美色給震驚到了當場!
“那是什麼?!”僧人向來處變不驚的臉上也有了輕微的失态。
那是一條流光溢彩的魚尾,那張海面上的臉,美得帶着一種不屬于世間的妖氣。
那是……人魚?
金色的長發比月色更耀眼,它遠遠地看着他,微微有些促狹地偏了偏頭。
僧人緊緊抓住了欄杆,他自幼飽讀經書,自然知道這世上有鲛人的傳說……可沒想到竟然是真的?
那條人魚看了他一會,突然沖他笑了笑,帶着等待已久的喜悅,張開口唱起了歌……
那是怎樣的歌聲?
仿佛能讓人忘記世間的一切不幸……恐怕就算是佛前的綸音也不過如此。
他眼前一黑,就這麼倒了下去……
吟遊詩人有些古怪地看了他一眼,“你說你看到了鲛人……不,人魚?”
“是的,”僧人微微颔首,“我聽說……”
吟遊詩人毫不留情地打斷了他,甚至還帶了幾分憐憫,“快醒醒吧,人魚這種生物雖然美貌,但是極其的兇殘。”
“在通往歐拉大陸的必經航線上就有一處塔比斯海灣,那裡就有人魚坐鎮,幾百年來除了猩紅玫瑰的夢魇号,沒人從裡面出來過!”
“最近的一次聽聞人魚的消息是在列支敦國的塔蘭朵思,教皇被魔鬼迷惑打算用人魚祭祀……不過也沒聽到下文,應該是成功了吧?”
……
不過嘲諷歸嘲諷,他還是恪盡職守的給僧人科普了一下猩紅玫瑰其人,然後才拿着自己的金币邊咬邊出了旅館,心中還慶幸宰了一頭大肥羊。
等他走後,僧人若有所思地思索了許久,忍不住苦笑了起來。
他必須要找到那條人魚……它從他的脖子上取走了佛珠,如果是旁的也就罷了,可偏偏那串佛珠當中有一顆是聖物舍利子。
那顆舍利子,是他最大的屏障。
他微微眯起眼,還記得在入海的一瞬間,他在冰涼的海水中稍稍恢複了一些意識,和那雙簡直是美麗的驚心動魄的眼睛對視了片刻,似乎還從中看到一絲疑惑?
随即……他更深的墜入了昏迷。
很顯然,人魚并沒有想要殺他的念頭,在他墜海之後從他脖子上取下項鍊以後遙遙用歌聲讓瞭望的水手清醒了過來,不過等他清醒過來看見僧人在海裡上下沉浮慌忙喊人來救人的時候,塔維爾早都不知道跑到哪去了。
什麼你問為什麼塔維爾不直接把人扔上去?
開玩笑,人魚從來都是兇殘名聲在外,不殺人還救人?生怕人不知道這個人有問題嗎?
潛伏在水下以防萬一沒人來救他活活淹死的小人魚默默想:……雖然光頭的确挺奇怪的。
塔維爾出現了,依蘭達當然也在左近。
當天晚上,向來隻在周圍活動的人魚意外地消失了大半個晚上,依蘭達倒也沒多替它操心。
反正在海裡能幹的過人魚的怪獸不是沒有,但是有那種戰鬥力的普遍沒有塔維爾跑得快,跑得比它快的普遍沒它能打,真要有什麼應付不了的怪物,這條人魚求救信号發的比誰都快。
第二天黎明的時候,依蘭達從夢中被人魚的歌聲驚醒。
她推開窗,塔維爾在海面上正興高采烈地唱着歌,它唱的太過于忘形,不自覺地就加上了人魚一族天賦的迷魂音效。
就連依蘭達也産生了瞬間的恍惚,沉迷在這天籁當中,直到周圍接二連三的撲通聲響起,女海盜緊接着立即反應過來,朝下面還在自顧自唱歌的人魚咆哮了起來。
“閉嘴!他們又跳海了!快把人給我撈上來!”
等到一陣兵荒馬亂之後,人總算都被救上來了,除了多喝了點海水之外沒有任何問題,塔維爾也知道自己做錯了,默默地把下半張臉沉在海水下,就露出一雙眨巴眨巴的大眼睛和直直立起的耳鳍。
一看就不是什麼正經人魚!
“塔維爾?”依蘭達又好氣又好笑地看着小人魚,“你這是在做什麼?”
命運從來都詭谲而不可預測,原本不會有任何交集的兩條線,在這裡展現出了可怕的不可操縱性。
小人魚默默冒了個頭,終于還是控制不住喜悅的心情,高高舉起了手中的一串珠子。
“依蘭達你看!”
在外面跑了這麼久,人魚的說話技能也日益點滿,加上日常打交道的都是尼卡之流嘴皮子極為利索的,整條魚的下限都下降了不少……更别提剛才用上的憑借美色來迷惑海上的人,把人騙的掉下海再趁火打劫之類能稱得上用頭腦而不是蠻力之類的手段了。
人魚的吐了吐舌頭,神情有些迷惑,“那個光頭我看着有些眼熟,但是實在想不起來什麼時候見過了。”
畢竟它活了數百年,見過無數的人和事,說的直接一點,死在它手中的水手都不知凡幾,指望它記得一清二楚……那也真是太為難它了。
女海盜借着晨光看了一眼,隔太遠實在沒看出來有什麼值得小人魚親自出手去坑蒙拐騙的地方,不免開始自我懷疑是不是最近太過于讓這條人魚放飛自我以至于連判斷能力都下降了。
“我沒看出來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依蘭達是笨蛋,”塔維爾打鼻子裡哼了一聲,尾巴憤怒地拍擊着海面,“如果是艾爾一定認識!”
依蘭達翻了個白眼,“那你找他去。”
反正艾爾這會還遠在奧斯公國呢,他倒是一直想東征跟着她出來看看,可很不幸,就算他現在成了教皇,很多事情也依舊不能以他的意志而轉移。
小人魚憤怒地用尾巴拍了拍水面,“這是舍利子!”
“那是什麼?”
依蘭達這下是真的茫然了,她雖然對金銀财寶的鑒賞力是出來了,但是宗教相關那真的是一頭霧水,就連教廷這邊的典籍也是因為艾爾才有所涉獵,約拿之書都是萬幸,更别提這還是東方的宗教的所謂聖物了……那是什麼鬼?!
塔維爾不知道怎麼跟依蘭達描述這個卡諾比曾經給它看過的東西,急的在水裡來回遊了好幾圈,“卡諾比以前曾經給我看過這個東西,他說,這是機緣!”
卡諾比?
依蘭達這一下是真有些注意了,這位阿爾貝托身上簡直充滿了謎團,影響力甚至跨越了百年,甚至可以說,一切有了現在的局面,他簡直居功至偉。
如果不是因為他,她和艾爾早在多年前就已經喪命在塔比斯海灣,更别提以後了。
“什麼機緣?”
小人魚搜腸刮肚想了許久,最終還是苦惱地搖了搖頭,“我想不起來了……”
記憶中的金發男人沖他露出了一個絢爛的讓他有些眼暈的笑容,“小塔維爾,你一定要記住這串佛珠,如果看到它,無論如何都要拿到手。”
“不管使用任何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