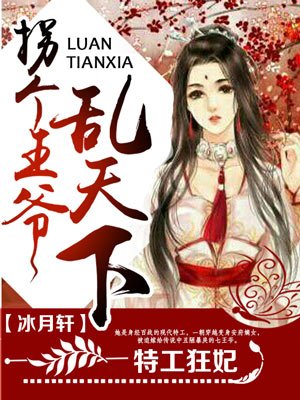林婆知道此事不能罷,她如今也打不過這些年輕力壯的小丫頭,隻得歎了一口氣坐在椅上。
安以繡看着林婆,仿佛是覺得椅子上有銀針似的,那林婆屁股來來回回的扭動,用一個成語來形容特别貼切林婆此時的行為,如坐針氈。
“常常,叫個人去問問隐禅院裡有沒有醫者。”
因為有林婆這個外人在場,安以繡和他們說話便也不會以真名相稱,算是比較隐晦。
白無常拍了兩下巴掌,立刻進來一個魅組成員,那魅族成員本想叫一聲閻王:“閻……”
卻在看到林婆之後,生生将那後面一個王字吞了回去:“夫人。”
白無常将安以繡的話轉達給那魅組成員,那魅組成員立刻領命離開。
在那魅組成員離開之後,房間頓時又陷入一種近乎于死亡的安甯,這種氣氛讓林婆很是不自在,雙手搭在扶手上來回的蹭了蹭,試圖挑起一些話題緩和一下氣氛:“夫人,叫醫者做什麼呀?”
安以繡沒有回話,隻把手放在腹部,不知道為何,她突然感覺此時腹部隐隐作痛,沒有勞什子的精力去回答林婆的話。
白無常已然認定林婆不是好人,兇神惡煞的瞪了林婆一眼,吓得林婆趕緊閉嘴,搖頭晃腦道:“這位姑娘,你瞪我做什麼,我也沒有問什麼其他的話吧,就是……就是想關心關心夫人。”
安以繡一直閉着眼靠在椅上,讓她們看不透她到底要做什麼,室内又恢複了一片甯靜。
那陣腹痛也不知道是心理原因還是怎麼回事,安以繡隻覺得自己休息了一會兒,陣痛又忽然消失,仿佛剛剛隻是她的錯覺,不論怎樣,還是找個醫者來看看,這樣也能放心些。
那個魅組成員的運氣不錯,在隐禅院找到了一個沒有去搶雪蓮花瓣的醫者。
隻不過那個老頭兒自稱醫者,行事作風卻沒有一點醫者的模樣,穿着一身灰色的破布衣裳,肩膀上背着一個磨得光亮的大葫蘆,也不知道他是窮了還是怎麼回事,他居然沒有穿鞋子。
光着一雙髒兮兮的大腳丫子就在地上随意的走動,都能看到他腳底闆起着一層黑色的厚厚硬殼子。
不管這人是不是醫者,至少他是隐禅院唯一能找到的自稱醫者的人,那魅組成員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把那老頭子帶到了安以繡廂房:“就是這兒,我家夫人需要醫者,請進。”
那老頭子把肩上背着的大葫蘆取下來,拉開了葫蘆上的木塞子,裡面傳出一陣濃香的酒味,他咕噜噜的喝了幾口酒,這才大步的跨進了廂房。
“你家夫人是誰呀?找我所為何事啊?”
一聲破鑼,嗓子在廂房之外響起,吸引了廂房之内所有人的注意。
安以繡看向那老者,幾不可見的掃視了老者一番,最後定在老者,毫不拘束的拿酒姿态上,那手上有老繭,這老者怕不隻是醫者那麼簡單,定然是個高手。
想至此,安以繡輕輕一笑,起身相迎:“是我讓手下人請您來的。”
“不知道請我來是要做什麼啊,這一房間的女人,啧啧啧,有些晦氣啊。”
那老頭子一邊說着,視線一遍打量着安以繡的廂房,毫不避諱的模樣讓笙玉看着都覺得心中有些不爽,剛想出聲教訓讓那老頭子收斂一點,卻看到安以繡制止的眼神,隻得将悶氣吞了回去。
“不知老者從我這廂房裡看到了什麼?”
雖說那老頭子行事作風有些瘋瘋癫癫,但安以繡卻從他話中聽到了一絲不一樣的意味。
那老頭子聽到安以繡這麼問,眼神之中閃過一絲贊許,點了點頭,毫不在意道:“還算有點小聰明。”
這下,就連白無常都微微皺起了眉頭,這瘋老頭子,是怎麼和他們在閻王說話的,一點尊卑概念都沒有!
但看到安以繡臉上并沒有絲毫惱意,反而沖那瘋老頭子做了個揖,白無常隻得等着看自家閻王到底是要做什麼。
“還請您解惑。”瘋老頭子繞着安以繡轉了一圈,拿着手中的酒葫蘆,将裡面的酒灑在廂房的四個角落裡:“給你灑點酒去去晦氣,行啦,小丫頭你倒說說,你叫我來是做什麼呢?不過先要和你說一聲,我出診的診金可不是
常人能付得起的。”
笙玉在一旁皺起了眉頭,嘴巴也跟着撅了起來,心中暗自道:這瘋老頭子能靠譜嗎?夫人這是怎麼了?居然對這瘋老頭子這麼禮貌?怎麼還不将這瘋老頭子趕出去啊。就連被白無常強制性壓在椅子上坐着的林婆,也都對這個瘋老頭子極盡鄙夷,林婆被憋了好一會兒,如今見到有個生人過來,自是要張嘴說說話的:“夫人啊,你有什麼事呀,若是要接生的話,這不是有林
婆我嗎?我是個穩婆,你說你的奴婢找這麼一個不靠譜的老東西過來,這不是……這不是……”白無常最讨厭的就是林婆在這叽叽喳喳的說些沒用的廢話,一個眼刀甩過去,吓得林婆又禁了聲,小聲和白無常解釋:“哎喲,哎喲,常常姑娘,我不說了,我不說了還不行嗎?你幹嘛要這樣瞪着我呀,怪
害怕的你這眼神。”
聽到林婆的話,瘋老頭子的注意力也被引到了白無常的身上,暗自說了一聲:“殺氣真重。”
白無常冷眼看着那瘋老頭子,對他的話并不作回答。
安以繡也不想接那老頭子這一茬話,索性說了找醫者過來的目的:“老人家,還請您幫忙看一下這個碗裡是否有薏米的藥性。”
笙玉有些詫異沒想到夫人是打算讓人看看有沒有薏米啊,可是剛剛她已經找過了呀,碗裡面并沒有薏米,夫人這是要做什麼啊?多此一舉嘛……
沒人注意到,安以繡說了這番話後,林婆的臉色瞬間變得難看。林婆眼睛直勾勾看着擺在桌邊的那碗紅豆蓮子紅棗粥,恨不得身上長一對翅膀飛到那桌邊将上面的粥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