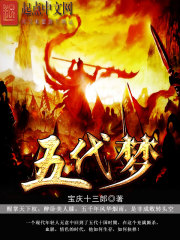馬車馳進陶家巷。
李昭成掀簾向後探了一眼。
“李郎君放心,那邊有人望風,沒有尾巴。”
“那就好。”
李昭成這才下了馬車,快步走進宅子。
“李節帥到了?”
“是,正在堂上與楊公說話。”
李昭成遂快步向堂上走去。
龜鶴莆快步趕到堂上,隻見賈似道正懶洋洋地倚在太師椅上,與廖瑩中說話。
“多年未見過如此拙劣表忠了,簡直不堪入眼。”
“必是遠不如阿郎。”
“莫拿他與我比,我待陛下腑腹忠誠。”
龜鶴莆上前,行禮道:“阿郎,查到了,吳潛回府之後,不多時果然有人出來,但跟到杭城大街,跟丢了。”
“跟丢了?”
“是,幾輛馬車堵在路上,等我們的人擠過去,人已不見了。”
“大半夜的,還這麼堵。”
賈似道笑罵了一句,轉頭向廖瑩中問道:“吳潛拿住的,是我們在追殺的兩個北人?”
“是,隻怕他馬上要查鄂州之戰。”
“那便讓他去查。”賈似道不以為然,悠悠道:“我賈似道學着童貫,虛報戰功,向忽必烈納貢稱臣,诓騙天下,自稱擊退十萬雄兵,我罪不可赦。吳潛若不敢徹查到底,他便是我乖孫。”
“看來,吳潛罷相不遠矣。”
“老東西比丁大全有手段。臨到入棺,倒還進益了,從前可是連謝方叔都鬥不過。”
廖瑩中道:“想必是老了還想多做些事,願意變通了。”
“想多做些蠢事。”賈似道譏道:“官家親生子嗣不出,不可能如老東西所願,絕無一絲一毫之可能。”
“太固執了啊。”廖瑩中搖頭歎息,又道:“如今李瑕亦投了吳潛?”
“三姓家奴。”賈似道難得沉思起來,緩緩道:“但不應該,李瑕本不該與吳潛沆瀣一氣。他分明知道,事到如今,吳潛隻有一條路走了逼李墉以死陷害忠王。”
“李墉一出面,李瑕必死。李瑕絕無與吳潛合作之可能。”廖瑩中沉吟道:“但現在,兩人真是合作了。”
“李瑕将李墉藏了?”
“吳潛豈能相信?”
賈似道緩緩問道:“那就是騙吳潛李墉是被榮王捉了?”
廖瑩中不由歎道:“若如此,這一手便有些老辣了,暫将不可能化為可能,搶出一絲間隙,掙出死局。”
“他想着回蜀掌兵,與吳潛目的相左,必将有大沖突。”
“那接下來,他又要借丁大全的力了?”
“呵,三姓家奴。”
廖瑩中起身,踱了幾步,沉思道:“李瑕搶占先機,自請還朝、自請辭官,吃準了陛下心思,步步為營啊。可惜阿郎便是看穿了他的謀劃,卻找不到證據揭破他。”
賈似道眼中泛着些許冷意,道:“此子根基太淺,做事太猖獗,已是危機四伏至于眼下,他不過是渡過了第一劫而已。”
“阿郎要出手?”
“不必,殿試之後,除丁大全;請立太子,再除吳潛。李瑕借此二人之勢太多、瓜葛太深,既是‘閻李丁當’,又是忠王死敵還敢想蜀帥之位,僅這兩場大争便要将他燒個幹淨。”
廖瑩中應道:“學生明白,會繼續派人盯着”
次日,風簾樓。
“李節帥請用。”
胡真捧起一杯清茶,雙手遞給李瑕。
李瑕接過,道:“胡媽媽太客氣了,我在臨安沒多少朋友,你算一個。”
胡真低着頭,恭敬應道:“奴家不敢當,奴家不過是風塵老鸨,李節帥卻是達官貴胄。”
當年,李瑕初次到風簾樓時,還能與胡真談笑幾句。
如今不同了,從縣尉到蜀帥,天差地别。
更大的差距在于,連風簾樓的東家,從關德到董宋臣,都已丢了聖心,還不如李瑕能在官家面前說得上話。
胡真不懂這些,但能體會到她的東家也要巴結李節帥。
地位拉開太多,她已不可能在李瑕面前談笑自若。
“哇,李縣尉真了得,人家要是再年輕十多歲,不收錢也想和你好呢請吧,别耽誤我做生意。”
這種玩笑話不會再有了。
“既如此,我這個達官貴胄就問一句。”李瑕道:“當初我離開臨安時,你說過親手養大的孩子,會盡力對她好人呢?”
胡真惶恐,慌忙便跪下來。
“李節帥莫怪,奴家開門做生意,有人來贖安安,勢力又大,奴家實在沒法拒絕。”
“賈似道将人帶哪去了?”
“隻知道不在臨安。”胡真道:“奴家派人打聽過,近兩年半點消息都無,必已不在臨安城。”
李瑕又問道:“你還在為董宋臣打聽情報?”
“是不過,如今這一行當,隻有教坊與風簾樓還是東家産業。其餘青樓、畫舫、書鋪、茶樓、酒肆,多有賈相公産業”
李瑕默默聽着,知道時隔三年再歸朝,閻馬丁當大勢将盡,已遠無當年氣焰。
胡真跪了一會,小聲問道:“李節帥想知道的,奴家都說了。關閣長已恭候多時,能否請節帥相見。”
“讓關德過來吧。”
閣樓上,白面無須旳關德不時揚起他的蘭花指,語氣又急又氣。
“咱們為何混成這樣?說來還不都怪李節帥要不是貴妃娘娘為你謀這‘節帥’二字,失了聖眷,至于嗎”
“季惜惜也是良心被狗吃了,咱們教胡媽媽花了多少錢養她?入宮後連盂盆都是金子做的,如今到好。成了對家的人,恩将仇報”
“李節帥,咱們可都是一條繩上的螞蚱,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你可莫忘了,當時中傷賈似道的信是誰遞的?沒了咱們,你鬥得過賈似道嗎?呸”
“眼下如何撐着?要不是憑閻貴妃多年養育瑞國公主的情份,咱和大官,早死八百回啦”
“丁相?丁相還不得靠咱們幫他說話,但好教李節帥知曉,丁相若要完蛋,不拉着你一起死,他枉生了那張青色面皮”
“總而言之,李節帥要咱們出力,總得想辦法先救了閻貴妃”
風簾樓一間雅緻香閨之中,有歌伎信手撥弦,開口唱起來。
“無謂兩眉攢。風雨春寒。池塘小小水漫漫。隻為柳花無一點,忘了臨安”
周震炎走進,聽着這詞,皺了皺眉,向歌伎道:“出去。”
“伏靈兄,怎了?”崔向青正聽得認真,不免覺得掃興。
“唱劉辰翁之詞,毫無眼力。”周震炎輕呵一聲,道:“這風簾樓是越來越不成了。”
崔向青不由詫異,暗想這般好去處,怎就不成了。
這話題聊不下去,他隻好給周震炎倒了杯酒,随口問道:“伏靈兄出恭怎麼去了這般久?”
“遇到一個故人。”
“誰?”
“李”周震炎輕呵一聲,淡淡道:“唐伯虎。”
“此人是誰?有名?”
“寫過一首歪詩。”周震炎譏笑道:“兩三年前傳遍臨安,你沒聽說過?”
“伏靈兄,我是今歲才入京考恩科的啊。”
“行在。臨安是‘行在’,你莫總說是‘京城’,讓旁人聽見,瞧不起你。”周震炎提醒道。
“好吧,行在。”崔向青道:“我就不明白,這行在和京城有何區别,為何一定就得稱‘行在’?”
“沒有為何。”周震炎飲着酒,像是在思忖着什麼,眼神漸漸焦燥起來。
“伏靈兄,你約我來,到底有何事?”
周震炎揣着酒杯,問道:“你恩科落榜,打算回當塗?”
“那當然,京行在,吃住實在太貴了,實不相瞞,小弟囊中羞澀,為了赴京趕考,借了不少錢财,萬萬沒想到,竟是不中。”
周震炎搖了搖頭,暗道中了才是怪哉。
他從袖中掏出一個荷包,推了過去,壓低了聲音,道:“幫我個忙,可好?”
崔向青打開一看,又驚又喜。
“銀銀的?”
周震炎修長的手指在桌上敲着,節奏很亂,問道:“答應了?”
“做什麼?”
一個瓷瓶又從案上推了過去。
“簡單。”周震炎道:“你回了當塗,到我家中,幫我妻子打水到水缸裡。”
“伏靈兄有妻子?小弟怎不知?”
“嗯。”周震炎道:“之後,将這藥倒進水缸。”
“然後呢?”
“然後。”周震炎傾過身子,道:“把屍體丢進大江”
“統制。”
一個漢子快步到閣樓下,對劉金鎖俯耳道:“那人說是來找唐伯虎的。”
“咦?他探頭探腦,不是在看大帥?”
“我湊過去聽了,說是看到了一個故人,叫唐伯虎。”
劉金鎖皺眉道:“我們這隊護衛,有人叫這名字嗎?”
“沒有。”
“讓老江跟了?”
“跟了。我還聽到這畜生說,他要殺妻”
劉金鎖聽得一愣一愣的,愕然問道:“殺妻?為什麼殺妻?”
“不知道,可就這樣殺,簡直都不知哪來的草包。”
“等老江摸清他們住哪,夜裡我去摁死他們得了,得和大帥說一聲。”
不多時,老江快步回來。
“統制,不敢跟了,那畜生後面吊着尾巴。”
“尾巴?”劉金鎖撓了撓頭,“這草包還能有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