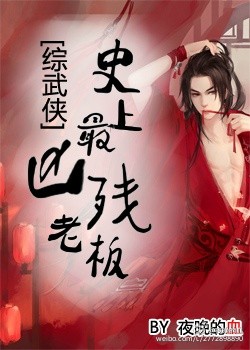就在我抛出經文阻擋惡魂時,不知從哪裡冒出來的陰兵已經占據了整條街市。不計其數的黑衣甲士陳兵城中,放眼望去到處都是黑壓壓的铠甲,唯有甲士手中的長槍冷芒熠熠。
我僅僅倒吸了一口涼氣,街上的陰兵已經擡起頭來。
“刷”――
數以千計的鋼槍破風而起的聲音,如同驚濤拍案滾滾而來時,足以驚鬼泣神的沖銷殺氣也陡然而起。那一瞬間,我甚至已經失去了思考的能力,隻是本能地覺得死亡将至,萬念俱灰。
“跪――”
無數陰兵同聲怒吼,聲浪如風卷地狂舞,我隻覺得腳下的屋頂在劇烈震顫,随時都可能在聲波的震蕩下崩塌。
“跪――”
陰兵再次怒吼之間,手中長槍齊齊高舉過頂,寒光閃動的槍尖,從四面八方指向了我周身要害。他們沒有動手,我身上卻莫名地冒出陣陣刺痛,就好像是提前感應到了長槍即将穿透我身軀的位置。
我偏偏在這時飛快地回頭,往杜渺那邊看了一眼。城牆上早就沒了他們兩人的蹤影,他們兩個應該是在陰兵出現之前就跳下了城牆。
不管他們能不能逃過陰兵的追殺,至少,我先前的布置也算給自己換來了一線生機。
“跪――”
數千軍士同聲怒吼,像是一聲平地驚雷,血城之内地動山搖,難以形容的殺氣仿佛凝聚成了有形之物,憑空向我碾壓而來。
我幾乎沒有猶豫,立刻雙膝一曲,跪在了房頂上。現在可不是逞英雄的時候。就算我能頂住滾滾而來的殺氣,又能如何?我能單槍匹馬掃滅血城,還是能單人獨劍殺出重圍?既然哪樣都做不到,還不如趕緊跪下換一條生路。
我雙膝剛一着地,街上的陰兵也同時收回了長槍。千萬支槍杆砸向地面的刹那間,轟鳴之聲震蕩天宇,陣陣黃沙如煙蒸騰,我腳下的房屋莫名其妙的被震了個粉碎。我隻覺得腳下一空,跟着斷裂的房梁摔進了屋裡。
我落地之後的第一件事兒不是挺身而起,而是趁機把白玉和灰灰給放了出去。兩個小家夥一離開我,馬上飛快地竄向了房角,縮成一團藏了起來。
我還沒爬起來,身上就多出了幾道鈎子――站在外面的陰兵,竟然拿着鐵鈎穿透了我的衣服,像拖魚一樣把我拖到外面,結結實實的捆了起來,押着走向了王宮的方向。
跟我一塊兒被抓的謝雨薇,臉色白到了極點,帶着哭腔問道:“李孽,你沒說我們會被抓啊!”
“被抓不是必然的結果嗎?”
我早就料到杜渺他們沖陣會引來陰兵――從古至今,就沒有哪個大型監獄不用重兵把守。或許那些軍士平時不會如何,但是一旦有人越獄,守衛監獄的士兵就會出現彈壓。
我也知道跟着杜渺他們一塊兒沖出去是最好的選擇,留下來就是拿命在賭。曆朝曆代對待越獄的重犯都可以當場格殺,尤其古代更是如此。我賭的就是血城陰兵不會一上來就對我痛下殺手。
謝雨薇的眼淚都流了下來:“你怎麼不早說?”
“我以為你能想到。”我該怎麼敷衍這個小丫頭?告訴她,我留下專門等着被抓的,你就該跟杜渺他們一塊兒跑?
“不對,你是故意的!”謝雨薇并不笨:“你是為了混進大牢,去救那個用鞭子的檀越對不對?你幹嘛要拽着我啊?”
我無可奈何地道:“要是讓你重新選一下,你是選擇跟杜渺他們出城,在沒有給養的情況下被陰兵滿沙漠的追殺;還是選擇留下跟我賭一賭會不會被陰兵殺掉?”
“我……”謝雨薇被我噎得不說話了。
押解我們的陰兵也從地上掀起了一塊鐵闆,指着下面的樓梯示意我們往下走。我剛低頭看了一眼鐵闆下面黑漆漆的樓梯,有人就在我身後飛起一腳,把我給踹了下去。
我大頭朝下摔在樓梯上之後,在慣性的作用下,頭部頂着樓梯倒立了起來,臀部朝下的再次滾了下去……我在樓梯上連着滾了三四圈之後,才重重的摔在了地上。
沒等我掙紮着起來,謝雨薇也一下摔在了我旁邊,沒了動靜。
“謝雨薇……謝雨薇……”我連喊了幾聲都不見對方反應,趕緊掙紮着往她身邊爬了過去,用肩膀撞了對方幾下。
謝雨薇沒動,我的領子卻被人給提了起來,拖在地上,走向地牢深處。那人一直把我拖進了一間相對開闊的屋子,才伸手把我拎了起來,用一根鐵鈎挂住我身後的繩索,把我吊在了空中。
直到這時,我才看見自己被人扔在了一間刑訊室裡。謝雨薇比我好些,沒被人吊起來,卻躺在了滿是血迹的青磚地上,生死不知。
坐在刑訊室正中間的位置上全身黑袍、用頭罩遮住面孔的怪人微微仰頭道:“敢對血城動武,你的膽子不小嘛!”
對方沒等我說話,就指着遠處道:“既然來了,就先歇歇腳吧,免得讓你說我血城不懂待客之道。”
我轉頭看過去時,第一眼看見的就是一張壓着釘闆的木床。
匣床?
我以前聽老核桃說起過大牢裡的各種刑具,這種匣床就是監牢大刑之一。獄卒把囚犯仰卧在床上,用鐵索固定四肢,鋼圈固定頭部,凡人就隻能躺在上面無法挪動身體,痛苦異常。很多人一旦躺上去就再也下不來了。
黑衣人看我發愣,不由得冷笑着拍了拍手:“給我們的嬌客鋪床。”
他話一說完,兩個身高差不多超過兩米、四肢異常粗大的獄卒就走了上來,扶住壓在匣床上的釘闆,同時較力,把釘闆給擡了起來。等我看清匣床上的情景時,不由得頭皮一陣發麻……
釘闆下面躺着的囚犯,雙手雙腳都已經被匣床上的鐵索給磨得露出了骨頭,卻偏偏咽不了氣兒,隻能眼睜睜地看着成片的蟲豸在他身上來回爬動,慢慢分食着自己的血肉。
我甚至看見一隻碩大的老鼠趴在他腳邊,旁若無人地啃食着他的腳指頭,就連看見人來了也沒挪動一下。直到其中一個劊子手輕輕地把它彈在地上,那隻老鼠才吱吱叫了兩聲,扭動着身子挪到了牆角。
兩個劊子手毫不留情地扯開囚犯身上的鐵索時,那人的身子才跟着抽搐了幾下。他顯然還能感覺到鐵索從自己四肢上抽離的劇痛,卻偏偏沒法兒掙紮,也無法喊叫,隻能本能地抽搐身軀,顯示自己的痛苦。
那兩人看都沒看對方一眼,抓着囚犯的肩膀,猛力一扯,生生把人從匣床上扯了下來。那人雖然離開了床面,背上已經被血黏在床上的皮肉卻被完完整整的撕了下來,血淋淋的貼在了床上。
直到這時,那人才發出一陣聲嘶力竭的慘叫,腦袋一歪,咽下了最後一口氣兒;也是到了這時,他已經分不清五官的臉上,才露出了一絲解脫似的笑意。
黑衣人若無其事地拍了拍手:“來呀,請嬌客安歇。”
一個劊子手大步走了上來,推着我身後的挂鈎,把我給挪到匣床上方之後,解開繩索,把我強行按在了床上。
從我被陰兵抓住開始,我身上的内力就一點兒也提不起來,沒有一絲一毫的反抗能力,隻能仍由對方擺布。
我跟匣床接觸的一刹那間,濃重的血腥味兒就沖進了我的鼻腔,還沒等我喘過一口氣來,原先被兩個劊子手吓得到處亂竄的蟲子就又都爬了回來,順着我的袖管、褲管鑽進了衣服裡,在我身上到處亂爬。僅僅片刻之後,我渾身上下至少有十多個地方傳來了被蟲子啃咬的刺痛。
這時,卻又有東西爬到了我的腳上――那隻耗子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