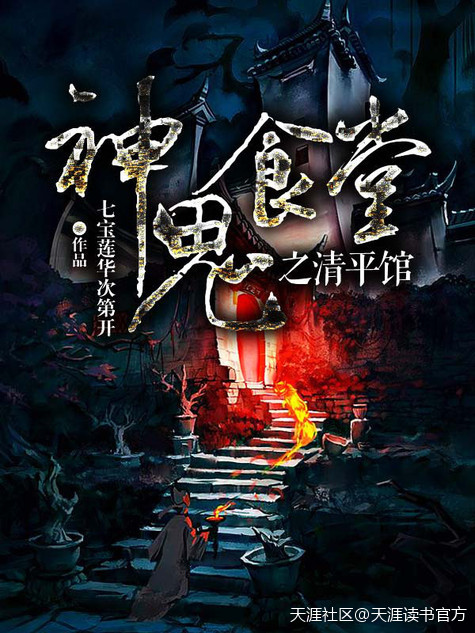第二百二十四回最愛涼晚佳客至,一碗菌湯下肚腸
綠楊垂壓,桃李間枝,湖内有各色魚不知凡幾,夜色之下,魚遊戲水,鱗挑月光,一位華服少年帶着幾個護衛坐在湖邊夜釣,丫鬟們打着扇子吹着香風,護衛們就着林木架起柴薪烤着白日裡打來的兔子等獵物,享受着春夜裡的半夜悠閑。
今日是谷雨,早上也果然下了雨,此刻尤帶濕潤的泥土有沁人心脾的芬芳,丫鬟們頗為興奮地發現,山林之中長出了好些香蕈來,忙不疊挑着品相好的采集來,打算熬一鍋尋珍湯,加些獵來的鹧鸪雀子。不多時,魚也得,兔也得,湯也得,埋在泥土裡做叫花雞的鹧鸪也走起噴香。華服少年心滿意足地坐在帷幔之中,對心腹們道:“五哥最會玩,這樣春風夜釣,新鮮食珍,配着這山水月色,果然顯得這樸素的烹調之法,竟有絕仙之味啊。”
那新生的菌子傘下還沾着點兒翠綠的苔,鮮得連鹧鸪肉的味道都聞不見了,華服少年心滿意足吃了好幾大朵兒香蕈,又狠狠啃了一條兔腿,一隻泥巴鹧鸪,吃了兩條魚才算完。
“王爺,快亥時了,咱們該回邈園了。”大丫鬟綠臘提醒。
春時兩山之茶,以龍井為最,明前龍井固然金貴,但谷雨的雨前龍井卻更易得些,因而也是廣受追捧,邈園裡的雨前龍井倒是新得的,朱橚兩口子便邀請幽篁裡衆人與鬼怪們一同在觀魚莊觀夜水高月,品雨前雀舌,一同吃個夜宵。
茶的确是雀舌,一芽兒兩葉,可今昭喝得不是滋味,她總能想起這個名字,也屬于一個神秘強大瘋狂可怕的人。
倒是利白薩這些日子耳濡目染,也有點見識:“這水可是虎跑泉?”
老周露出譏笑:“泉水烹茶,講究鮮冽,虎跑泉運到這裡,還能鮮?你以為你的大自然的搬運工麼。”
利白薩嘿嘿笑:“要是虎跑泉這樣好,我還真願意跑一次,搬運點兒虎跑泉回來。”
“筍鮮來了!”今昭拍手。
幽篁裡雨後的春筍新鮮摘下,用金花腿燒炖,以竹葉為柴薪,那種鮮美自然的滋味,仿若風搖碧浪,雨過綠雲,雉歌春陽,鸠呼朝露,那種清澈開明,綠意滿兇。委實能令人多添一碗好飯。
正吃得酣暢淋漓,忽然有鬼仆來報:“王爺,齊王殿下,突然腹痛如絞,已經昏死過去了!”
嘩啦——
無邊豪雨同時自天際潑落,朱橚霍地起身:“良醫如何說?”
鬼仆一臉凄惶:“劉良醫已經開了藥,卻束手無策,李良醫又趁夜去瞧,卻說,卻說齊王殿下印堂陰晦不明,恐怕是鬼祟!”
朱師傅與玉卮蔓藍鬼王姬四人起身:“我們也去看看吧。”
朱橚的弟弟齊王朱榑是因為身體不太好,前陣子來邈園療養遊玩的。朱橚瞧着他一身陰祟之氣,應當是宮裡沾染了太多,便竭力相留,朱榑便不再推辭。這些天來遊山玩水,接近天然,本來是已經大好了,傍晚時分還去湖邊夜釣取樂,誰曾想不過是半個晚上過去,這會兒那溫潤少年,便成了一個面色蠟黃,生氣了無的軀殼,除了心腹處還有起伏,簡直已經看不出他還活着。
“花李郎,在我們面前便不要藏掖了,你以為何?”朱橚瞧着戲子鬼那副欲言又止的樣子。
那戲子鬼重重歎口氣,朱橚這會兒也摸出了端倪,兩人面面相觑,朱橚無奈扶額:“總之,先不要再催吐了,恐怕吐不盡,更麻煩。我先下針,穩住了再說。”
朱師傅拿起桌子上那張丫鬟寫的飲食單子,上面列着今日齊王朱榑吃過的所有的東西,朱師傅在夜釣野味那一塊兒仔細看了看:“派人去了麼?”
戲子鬼點頭:“凡今晚的魚肉菌子,都令人去采了來。”
朱師傅面色泰然:“放心,他是死不了的。我為齊王之時,曾見起居記錄,第一代的齊王能獲得異能,便是因為與仙人有緣,習得仙術,後名義上廢為庶人,實際則依舊以齊王之尊起居,為朱家皇族驅鬼問神。他若是在此時死了,曆史的道标,便會不一樣了哦。”
蔓藍和鬼王姬瞧着朱師傅臉上的笑容,齊齊打了一個寒戰。
是時,那些魚也從同一個池水裡撈了數條,那兔又捉了一窩,那菌子也采了好些籃,剖魚宰兔切菌子,想要瞧瞧是否這些食材,有什麼端倪。
清平館一幹人齊齊圍在齊王住的客院淡山涼晚,瞧着陳清平以分花繡錦的細緻手法,将那些食材一一解剖開來。不一會兒魚和兔已經都片了片兒,陳清平幹咳兩聲,一番刀工剝皮剔骨後,手指間隻有淡淡血水,那些主要經絡血管,竟然還留存不破,相連如常。衆人各自去查驗這些池魚兔子,最終,一無所獲。
衆人面面相觑,各自歎息,陳清平一擡手攔住鬼仆:“等下别丢。”
今昭以為陳清平有什麼發現,也伸着脖子去看鬼仆手裡收攏起來要丢掉的魚肉兔肉。
陳清平擡頭,神情專注:“此魚鮮嫩,兔肉肥厚,一會兒吃了吧。”
今昭一個趔趄,差點跌倒:“……”
衛玠眉頭微蹙,轉向那一段樹木:“再就是這些菌子了,這些東西不過是一個晚上催生,這樹也并無問題……”
“那問題,就是這些菌子麼?”今昭拿起一個香蕈來,還未湊在眼前,就被陳清平劈手奪下。
太歲隻覺得眼前一花,那香蕈就已經落在了案闆上,被陳清平的刀插了一個正着。
切開的香蕈傘滿尾肥,一看就是春日裡吃飽水分的好貨色,然而從頭到尾,這香蕈也并無不同。
“有什麼問題?”利白薩覺得中國的神神怪怪真是腦洞大開,吃個野餐也能吃出毛病來。
“适合炖雞。”陳清平很直白地回答。
“……好吧,姑且都切開看看。”今昭提起那籃子香蕈,一個一個擺出來,也不知道擺到了第幾個,忽然有一個聲音罵:“兩個蠢材鳴翠柳!一行仙家窩裡瞅!”
那聲音很小,弱不可聞,要不是今昭是太歲,又離着香蕈很近,大約也會聽不到——除了陳清平,似乎别人都沒有聽到,還在談論着旁的事情。
陳清平低頭看了看已經切開的香蕈,又看了看今昭手裡的那一枚,極快地奪過來:“不要再碰。”說罷,幹脆連整個籃子都搶了過來。
今昭一臉茫然。
陳清平微微瞪了瞪眼:“站遠點。”又看了看今昭一瞬間的苦臉,“有古怪,你往後站站,不安全。”
今昭正要反駁她好歹也是一隻太歲,卻又聽見那個細弱的聲音用一種唯恐天下不亂的語氣喊着:“呦呦呦!昨夜星辰昨夜風,今日奸情廚房中!”再聽這聲音,的确是很有古怪,因為聽上去雖然細弱,可并不像是一個人喊出來的,反而像是好多人一起喊出來的!
哪來的“好多人?!”
陳清平與今昭面面相觑,視線一撞,兩人都有點覺得臉熱。
那個聲音又細細地喊:“白日依山盡,奸情入海流!欲懂少年心,還請褪褲頭!”盡管聲音依舊很小,卻喊出了粉絲們看演唱會的氣勢來,萬人齊聲。且這内容之下流,簡直令人不忍直視!
今昭循着那聲音,終于發現,那聲音是從陳清平手裡那個蘑菇裡發出來的。
陳清平示意大佬們過來看,自己則棄刀不用,捏住那香蕈,輕輕一掰。
“啊——”以老宋為首的密集恐懼症患者們紛紛倒地。
那蘑菇一掰開,便能瞧見,蘑菇傘下沾着好多的青苔,而那些青苔一直沁入了傘内,一掰開那蘑菇,便有好些極其小極其小的東西,從那些青苔鑽了出去,在案闆上列陣,鑄起了一塊兒一塊兒的青苔,鑽在青苔裡不見了。
朱橚眼疾手快拿起刀,從案闆上刮下一塊兒青苔,将刀刃橫起,湊上與衆人細細觀看。
隻見那刀刃上的青苔裡又跳出好多的那種極其細小的東西來,因為刀刃是金屬,似乎也沒有辦法做青苔為堡壘,那些小東西便站在刀刃上破口大罵:
“愚民!愚民!驚起一傘菌露!”
“兩屋蠢貨裝不住!一廚愚民翻過山!”
“問君能有幾多蠢!恰似汝等愚民炕上滾!”
“嘈嘈切切錯雜彈!汝等白爛裝上盤!”
“朝來寒雨晚來風!智力謝了秃頂太匆匆!”
“垂死病中驚坐起!不忍見汝智力無!”
“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汝腦殼塞住!”
透過朱橚拿出來的透鏡,這些細小的生物細細看去,分明是毫厘高的小人兒,眉目俱全,錦衣華服,各個捧着心口在高聲叫罵,音色齊整如一,氣勢表情都十分澎湃。而那些苔藓,也根本不是苔藓,而是類似于鞭子披風刀劍之類的綠色兵刃,隻是因為太過細小,簇擁在一起,才看上去像是苔藓。
“這是……菌人?”衛玠表情頗為玩味,“拿些上等菌子來養着,不然這群小東西報複起來,可是十分麻煩的。尤其不能害其性命,用毒用藥。”
朱橚瞧着這些小人兒的大小,面色一肅:“可有什麼法子,既不會傷及這些人,又能讓他們離開齊王的肚子?”
衛玠看了看這些菌人,搖了搖頭:“菌人喜歡珍稀菌菇,也許用菌菇引誘,是個法子。然而以齊王的狀況,若不盡快,隻怕有性命之憂。”
“若是開腹,以菌菇誘之,這是白澤的手劄上記載的罷?”朱師傅皺眉問。
衛玠看了看朱師傅,又看了看朱橚:“值得一試,隻是,你們誰會開腹?”
黃衣鬼眉開眼笑:“王妃會啊!王妃連斷手斷腳都能縫回去!”
麻衣女鬼一推黃衣鬼,推掉他頭顱,啐道:“王妃懷着身子,這幾日就要臨盆,如何能行這等熬心血厲之事!”
黃衣鬼的頭不服地在地上滾着叫:“可是王爺,若是齊王在咱們這裡出了事兒,咱們的麻煩,可就不是改個封地能解決得了!”
“我來。”陳清平突然開口,“牛取黃,狗取寶,鹿取麝,事同一理。”
衆人還未反應過來,那菌人的大合唱又響起:“八毫厘刀,血和肉,三刻鐘時候,活與死!王師北定中原日,廚子你是好漢子!”
“……”
“雲想衣裳花想容,開腹一寸可就行!”
“積雨空林煙火遲,肚裡蘑菇塞一隻!”
“莫愁前途無知己,等個一刻再洗洗!”
那些菌人在諸人置辦開腹事宜的時候,齊聲高唱,聽那唱詞的内容,卻是好心意地指導,應該怎麼做。隻是這唱詞實在令人無語,就是淡定如陳清平,也在洗手的時候聽見“血沫乳花腹上沾,好帥廚子切腹難!”這句時,差點将手裡的胰子給丢出去。
待到要行事之際,各色物件已經備齊,一應沸煮以秘藥消毒,陳清平兩眼一閉,再睜開的時候,大家覺得陳清平瞧着齊王朱榑的表情,已經和瞧着一頭死豬沒兩樣了。有見識的幾位在屋子裡給陳清平打下手,今昭這種宰割兔子都嫌棄手軟的,留在外面為男神掠陣——主要是負責不要讓菌人們接近那件屋子,否則正在開胃的時候聽見一句“無可奈何花落去,一隻王爺活不來”,估計陳清平會順手把胃給摘了。
“自在飛花輕似夢,活着出來真高興!”
“春江潮水連海平,好好出來那就行!”
一番手術做完,藏在蘑菇裡跟着出來的另外一批菌人與原來那一批相見歡,今昭嘴角抽搐,原來菌人說話都是這樣,這不是部族特色,而是民族特色啊!
一時間有玉卮朱師傅衛玠陳輝卿這樣的高手在,又有朱橚本人和戲子鬼花李郎,齊王已經安然無恙,原本應該出現的傷口,也因為大神的時間法術而根本沒出現過。隻是不多會兒齊王醒來,嚷着好餓好餓,那是因為他的身體時間調成了谷雨這日夜釣之際,那會兒他剛撐好魚竿,還沒吃那一肚子珍馐野鮮。
這些之于今昭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陳清平體力不支,又需要小太歲去二十四孝,端茶遞水。
瞧着陳清平,今昭欲言又止。換做從前,陳清平對這種事情應當是不聞不問的,更不要說像今天這樣,原本身體不行,還要勉強去做。
也許是她遲鈍,也許是她多心,可是這一刻她真的發現,原來以為會一直那樣高踞神壇,烹饪天下的人,已經在她沒察覺的時候,開始慢慢改變。
啊應當不會變成朱師傅或者老宋吧。
太歲不僅腦補了一下陳清平笑得溫柔腹黑,或者笑得陽光燦爛的樣子,片刻後,她打了一個寒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