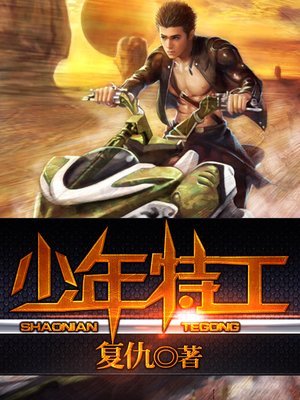冰龍已經躺了好一會兒——至少它覺得是很長的一會兒了,可它的力量恢複得如此緩慢,慢得它幾乎都感覺不到。
這不正常。
它是天生的魔法生物,這個世界本身就是它的力量之源,但當它用心去感知,它發現它周圍的力量幾乎被掠奪一空。
那法陣或許是被截斷了一部分,或許并未能完全運轉起來,但無論是否有人操縱,它都瘋狂地吸收着一切它能吸收的力量,先是魔法之力,然後是生命力……此刻,連它靈魂之中的永恒之火,都警惕地把自己縮成了小小的一團。
而當它看向白鴉,它意識到,她的力量也是一樣,被一點點吸收殆盡。
她的确成功地讓那法陣的循環出現了小小的缺口,但最終,她為此而施放的力量,連同那些薔薇花枝的生機,卻都還是回到了那循環之中。
她能夠延緩那過程,甚至因為她那誘餌般的力量的吸引,整個法陣或許放棄了更加瘋狂的攝取,而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與她的争奪上,卻更像是某種好奇的遊戲——她根本無法阻止法陣的力量變得越來越強大,更别提徹底切斷它。
她支撐不了太久了。
白鴉輕輕地笑了一聲。
“如果我離開,”她說,“你隻會在那裡躺成一堆白骨。”
冰龍都能感覺到的事,她又怎麼可能不知道。
“我不需要……”冰龍惱怒地開口,卻立刻被女法師打斷。
“我高興。”她說,“不是為你。是我自己高興。”
冰龍氣得說不出話。這種……讓人咬牙切齒卻又無可奈何的任性,實在很容易讓它想起星燿。
“如果你還有力氣在那裡說廢話,或者想些有的沒的,”白鴉懶懶斜它一眼,“不如想辦法提醒一下你那位朋友,如果想要弄死什麼人,最好下手快一點……他的力量,也許沒有你的那麼可口,卻應該也是很受歡迎的呢。”
……這又是什麼鬼話!
冰龍低吼一聲,居然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在重新摔下去之前,它變回了人形——這小小的形體需要消耗的力量,要比巨大的龍身小得多。
他望向三重塔。距離并不是很遠,但錯落開裂的地面,滿地碎石和倒塌的樹木,仍不是噴起的水柱,對此刻的他而言,居然也成了難以逾越的阻礙。
“難以”,不是“不能”。
他惱怒地告訴自己,在邁步之前,不由自主地又看了白鴉一眼,最終卻什麼都沒說。
半枯的薔薇花枝在他眼前散開,也為他指出一條最快的路。
他跑了起來,越跑越快,再也沒有回頭。
.
白鴉輕輕吐出一口氣,在感覺到連那口氣都在微微顫抖時惱怒地蹙眉。
她都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堅持到現在。她已經盡了身為“老師”的責任,她完全可以轉身離開,把這個亂攤子扔給那些還在城堡裡亂跑着救人的聖職者……他們大概都沒意識到自己的力量也成了這個法陣的養料。
她用薔薇花枝把他們阻隔在外,遠離最危險的地方……但說不定,此刻在他們看來,她很有可能是這場災難的罪魁禍首,或至少也是同謀。不然,她幹嘛要攔着他們呢?
她撇撇嘴,自嘲又不屑。
沒錯,哪怕是為了打腫那些人的臉,她也得再堅持一會兒。說不定那兩個小家夥就能力挽狂瀾,又說不定那幾個老家夥真能撞上什麼大運,破壞掉這個法陣呢。
到時候,她可要好好地欣賞一下那些驕傲的大白鵝們臉上的表情。
她動了動發僵的手指,再次集中精神。風漸漸大了起來,在周圍胡亂地旋轉着,沒有方向地亂撞。她的頭紗被風吹走,但她已經顧不上那個了。
反正也沒人看見。
她想着,片刻之後,忽地一僵。
她緩緩轉頭,看向斷裂的長廊邊,一個蹲在廢墟上的老頭兒。
一頭白毛遮得他的臉都看不清,一雙眼睛卻灼灼地看着她,其中是不帶半點掩飾的傾慕與熱切。
“美人!”他高高舉起雙手,大聲叫着,站立時兩條腿卻仍奇怪地微彎。
白鴉眯了眯眼。這不是那個變成了兔子的瘋法師嘛?他怎麼又蹦出來了?
她對羅穆安·韋斯特倒說不上有多麼崇拜,隻是有幾分好奇。然而此時此刻,心知肚明自己是什麼模樣,那點好奇也不能阻止她冷笑,故意扭曲了臉,惡聲惡氣地問:“哪裡美?”
是滿頭的白發還是滿臉的皺紋,抑或是幹癟收縮的牙床?
羅穆安交握起雙手,眼睛亮晶晶的,聲音洪亮,回答得無比認真:“骨頭美!”
白鴉怔了怔,終于忍不住笑出聲來。
她笑得彎下了腰,好不容易又扶着腰站直,再不顧忌臉上堆疊的皺紋,笑容肆意而張揚。
“那麼,”她說,“不來幫個忙嗎?要不然,你的骨頭美人兒,可就要變成骨頭渣啦。”
.
一位水神的聖騎士匆匆而來,在伊卡伯德耳邊低語,讓他原本就難看的臉色更黑了幾分。
“發生什麼事?”約克·特瑞西直截了當地問道。
現在可不是得斟酌着禮儀之類的東西,說句話都要小心翼翼先在心底過上三遍的時候——他們沒有個時間,更沒有那個閑心。
伊卡伯德倒也沒有拒絕回答。
“羅穆安又跑了。”他說。
約克本能地吸了口氣,卻又覺得,這種時候,這好像也不算什麼大不了的事了。
“我們的人差不多都已經撤出來了。”他環顧四周,“除了埃德和那條冰龍,白鴉……還有那幾位‘冒險者’。”
倒不是他有意不敬。包括昆茨在内,那幾個老頭兒的确都曾經是頗有名氣的冒險者,但他們畢竟已經老了,為什麼就不能安心待在家裡養老呢?今天的麻煩都不知道是不是他們東挖西挖給挖出來的……
“那幾位‘冒險者’,”巴爾克接口,“已經鑽回了地底,試圖解決問題。”
他看了年輕的大祭司、光之劍的持有者一眼,那意味不明的眼神讓約克不由自主地站得更直。
“而那位夫人,剛剛救下了那條龍。”巴爾克繼續說着。這一片混亂之中,他的消息也并未斷掉,但他剛剛得到的這些,大概也是他最後能得到的了。
他的人要麼已經撤了出來……要麼再也出不來了。
【領現金紅包】看書即可領現金!關注微信公衆号【書友大本營】現金/點币等你拿!
“據他們猜測,洛克堡地底有個古老的法陣被激活……這與我們那位好國王有關,或許還有其他人在暗中行事——一個極為年輕的黑袍法師,或許是他的幫手,又或許是真正的主謀。”
老人的眉頭擰了起來。這的确是他的疏漏,他輕視了那位國王……盡管他加強了防備,甚至不允許那幾個老家夥在夜晚到處亂挖,但他忘了,對安特來說,白天和黑夜其實沒什麼區别,而他雖然總是孤零零地在地底遊蕩,他的背後,卻也并不是沒有其他的力量……
他也想不通那個裹着一身黑袍的少年是怎麼鑽進來的,隻能歸結于魔法——也許他該對魔法更多一點尊重。
而那年紀不大的家夥下手比安特還要狠,為他傳出消息的人都沒能逃出來。
老人背在身後的手不自覺地握緊,語氣卻依舊平穩:“我覺得我們可以再等等,沒有必要那麼急着把整個洛克堡封起來……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那應該也不是一勞永逸,或毫無危險的吧?”
約克語塞。他也沒說要盡快封住洛克堡啊!畢竟埃德都還在裡面,伊卡伯德也……
他飛快地看了面無表情的牧師一眼——伊卡伯德大概不會以此作為判斷的标準。
此刻,牧師正盯着那座黑色的高塔,又收回視線,緩緩掃過幾乎成為一片廢墟的洛克堡。
地面仍在震動,中間雖有片刻稍稍弱了下去,但很快又強烈起來。那節奏越來越快,快得讓每個人的心跳都随之改變了節奏,急促得怎麼也平靜不下來。
洛克堡的大門内原本是一片空地,如今也已一片狼藉。碎裂的石闆混在泥水之中,鋒利的斷面斜斜切向天空,淡紅色的水流依舊汩汩而出,蜿蜒流向他們腳下,又被無形的屏障所阻攔,不得不尋找别的出路,曲曲折折才流了出去。
是的,他們其實已經開啟了屏障,以阻擋洛克堡内橫沖直撞的、混亂的力量狂湧而出,摧毀整個斯頓布奇城。但這屏障并不是一堵堅固的高牆,而是如花瓣一般一層層錯落的盾牌,将撞擊而出的力量一點點卸掉,而不是強行禁锢起來。現在看來,洛克堡瀉出的力量并沒有他們擔心的那麼強大……可這一重重屏障,被消磨的速度,卻又比他們預料的要快得多。
約克心中生出某種懷疑。當他想着該如何開口的時候,伊卡伯德的聲音響了起來。
“将所有的屏障往後再挪三十尺,”他說,“分散一些……不用再增加。”
這屏障本就是他所設,其他神殿的聖職者不過是協助,雖然有些疑惑,卻也并未反對,隻是将他的命令傳了下去,等待指令統一行動。
而約克忍不住眼睛一亮。認識以來第一次,他似乎跟這位摸不透也不好打交道的牧師想到了一塊兒……居然控制不住地有點激動。
“你覺得……”他開口。
伊卡伯德淡淡瞥了他一眼。
“肖恩回不來。”他說,“這裡的聖職者大概更願意服從你。我需要兩隊聖騎士,不需要魔法的幫助也足夠優秀的那種,一隊由水神神殿來出,一隊……”
“我來組織。”約克一口答應。
而伊卡伯德又轉向了巴爾克:“那幾個冒險者的位置……”
“我派人帶你們去。”巴爾克立刻開口。
伊卡伯德滿意地點點頭,臉色總算好了一點——不用把話說完就能被聽懂,實在是太省心了。
他再一次望向三重塔。埃德向他提起過塔頂的那扇門,他并不是沒有興趣,隻是實在沒有時間分心去處理更多的事,想着那扇門兩百年來都沒能打開,應該也不會那麼容易被打開,也就暫時沒去理會……
那或許是個錯誤。
而現在,在他們趕去之前,希望埃德能守住那扇門吧。
.
埃德正在絞盡腦汁地想辦法。
作為一個施法者,他似乎經常需要在“不能随便施法”的情況下戰鬥,如果這是某種“磨煉”,他實在很想對設下這種磨煉的不管什麼神吐口唾沫。
……不,吐唾沫好像也太失禮了一點,翻個白眼應該還是可以的吧。
這麼一退,因為惱怒而生出的那點氣勢立刻就沒了。他險而又險地從安特的長劍之下閃開,看着一縷白發紛紛而落,驚出一身冷汗。
但他在躲躲閃閃中設下的法陣已經完成,即使隻是個“速成”的法陣,也總能撐一陣兒。
時間拖得越久,情況隻會越糟……他無論如何也得盡快解決這兩個家夥。
他把一顆海藍寶石砸碎在正确的位置。微光閃過,空間一陣扭曲。霍安警惕地後撤,那點異樣卻已經消失。
少年驚疑不定,本能地想要躲得更遠一點,十幾支火箭已經拖着耀眼的軌迹,沖他直紮了過去。
霍安臉色一變。埃德已經有好一會兒沒有施放過攻擊力如此強大的法術,像是在顧忌什麼。
他展開雙臂,飄飄蕩蕩地滑開,那十幾支火箭卻緊追着他不放,其中有兩支撞在了無形的屏障之上,微微一閃便熄滅消失。
少年若有所思地望向那兩扇他始終沒法打開的門。
之前他隻是有所猜測,現在卻差不多可以确定埃德到底是在顧忌什麼。
他在安特向前攻擊的時候轉來轉去,像是在努力躲避那些魔法箭矢,最終成功地讓它們大半落在了屏障之上……而這屏障似乎相當脆弱。
當他停下來的時候,埃德已經靠着一陣猛烈的、肆無忌憚的攻擊将安特轟翻在地,卻又在明明可以徹底解決敵人的時候不自覺地猶豫了一下。
少年嘴角裂開,笑了起來。
他一直覺得,這個人,如果沒有他的保護,總有一天會死在他總是不合時宜的心軟上。
那一刻,或許,就是現在。